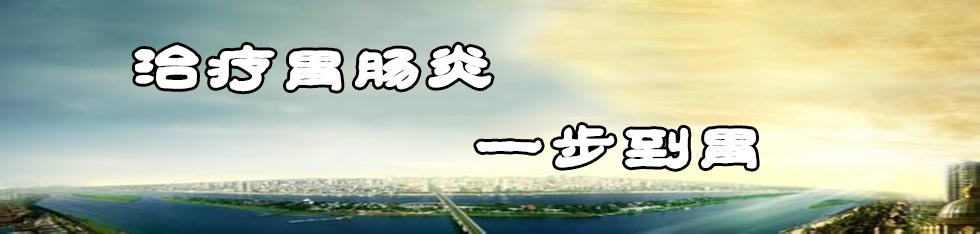
“让阳光沐浴在生命的最后一公里。”
走进医院,上至四楼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长长的粉红色走廊。走廊的正前方,用绿色字体书写的标语赫然显现。
医院一共8层,其中4—8层都是这样的设计。这五层楼单独成为一个病区,人们通常称其为康宁科——健康安宁,人类的终极追求之一。来到这里的人,除了行色匆匆的医护人员和义工,大部分便是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的高龄临终病人。
医院的护士告诉我,一般情况下,楼层越高,病人的情况就越严重。在这里,楼层的高低,无情地宣判着生命最后一公里的冲刺速度。
作者
王雅婷
责编
何小菊
图片
受访者、网络
01艾草婆婆
“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?”
“至今为止,你印象最深的关于死亡的经历是什么?”
在广州十方缘开的一家咖啡馆内,十几个临终关怀义工围坐在咖啡馆正中间的一张暗红色大桌旁,双眼盯着桌子前方PPT上的问题,陷入了思考。现场很安静,暂时都无人开口说话,唯有缕缕咖啡香将人的思绪牵向远方。
这种定期组织有关“死亡”话题的讨论的咖啡馆,被称为“死亡咖啡馆”。在死亡咖啡馆内,死亡不再是禁忌,一切有关死亡的经历和见闻,都可以在这里被谈论。
年,广州十方缘共举办了十六期死亡咖啡馆活动,我参加了其中的十期。据活动组织者芝麻介绍,死亡咖啡馆并不是中国的“土特产”,而是起源于英国,是一种“舶来品”。
年9月,英国人JonUnderwood组织了全球第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。此后,死亡咖啡馆在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先后出现,并形成一股小小的风潮。我国的第一家死亡咖啡馆则出现于年,由两位临终关怀领域的公益人创立于北京77文创园。
死亡是什么?我们又如何看待死亡?
换作两年前的自己,我很可能对该问题无动于衷。在我这个20多岁的青年看来,死亡未免太过遥远和让人惶恐。直到至亲爷爷的去世,我才来得及和死亡打了个猝不及防的照面。死亡的突然闯入,迫使我开始正视它、思考它。
机缘巧合下,我成为了广州十方缘的一名临终关怀义工,并参加了由义工芝麻组织的死亡咖啡馆活动。
一年多的义工经历,让我见证了无数的生老病死。面对着PPT上的问题,昔日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,在我的头脑中上演着一幕幕生死离合。在众多的故事片段间,在时光的长廊处,一个散发着艾草香的老人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。
图为医院
年11月的一天,我照例来到医院进行义工服务。径直走入7层,正准备去看望老朋友军哥,一阵浓郁的艾草香便扑面而来。“十一月怎么会有艾草香?”我心下纳闷,脚步一转便去寻那香味的来源。
走至病房前,定睛望去,只见一中年女子正半蹲在床前替病床上的老人做艾疗。然而,艾草烟雾冉冉却也抵挡不住老人身体创伤的可怖。老人全身都被白纱包裹,形似木乃伊,伤口渗出的血将白纱染红,凝结成大小不一的血斑,露出的双脚和右手掌的皮肤已经萎缩,状如黑炭。
一眼看去,我只感到头皮发麻,毛孔骤缩。生命有时太过脆弱,医院,这份脆弱也能在一瞬间唤起潜藏在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
老人是烧伤,事故仅仅发生在家人离开短短两分钟后。对此,老人的家人都很自责。尤其是大女儿,在老人刚住院时,由于放心不下,每天白天照顾母亲,晚上照顾孩子,白天晚上两个地方连轴转,十一二点才能休息。艾辽,便是她想出来的办法。
虽然不说,但医院的人都知道老人活不长久——老人年纪大了,这次烧伤又伤及内脏,治愈的希望很小。只有大女儿笃定老人还会醒来,面对旁人放弃治疗的劝告,她只是说:“这是我妈。”
我也时不时去看望老人,这不仅是临终关怀义工的工作,也有我的私心。不知为何,初见时的艾草香始终萦绕在心间,忽远忽近,提醒着我病床上还有一个烧伤严重的老人。
一次,站在老人的病房前,一个护工委婉地提醒我:“她(指艾草婆婆)说不了什么话,去陪别人吧,陪别人还有些作用,有的老人还能说点话。”我轻轻摇了摇头,简单解释后便静静地站在一旁不再说话。
医院里最不缺的就是死亡和离别,护工们早已见惯。但临终关怀的意义就在这里,对死亡永不冷漠,对生命永怀敬畏,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离开。即使生命将逝,即使无法言语,临终之人也有作为人的对陪伴和关怀的渴求。
走进病房,老人的精神出奇的好,看见我来,吐出一口白话:“多谢你。”我冲她一笑,点了点头,只静静地陪着,不作过多的打扰。有时候老人实在是痛苦极了,身体的痉挛带动着病床一齐颤动起来。
这时候我却只能看着,她很痛苦但我什么都做不了,唯有给出一句苍白的安慰:“这么不舒服,太辛苦你了。”老人的眼神微微闪烁,我听到一句喃喃低语:“是啊。”
一周后再来,老人的床上已是空空如也,我心下了然,但仍抱有些微希望,赶紧上前询问路过的护工,果不其然,得到的消息确凿无疑,老人几天前就走了。
“具体什么时候走的?”
“记不得了。昨天或者前天走的吧。”
微风吹来,空气中满是艾草香。
图为医院标语
02和死亡对话广州十方缘开展的死亡咖啡馆活动,每一期都有着不同的主题。
年4月,受疫情影响,死亡咖啡馆活动在线上开展。恰逢清明节,活动主持人芝麻便将主题定为“所在地区的殡葬仪式和风俗”。
这一期活动,菲姐格外活跃。作为一个从事殡葬行业十多年的殡葬师,谈及殡葬仪式和风俗,菲姐最有发言权,话匣子被打开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。
我坐在角落里,静静地观望着,时不时出声附和,但并不怎么言语。看着菲姐神采飞扬的样子,我却想到了她曾经的故事,一个并不属于这一期活动的故事。
其实,菲姐在早年并不是一名殡葬师,甚至其前期的工作和现在的殡葬师工作毫不沾边。她在工作上如此巨大的转型,来源于一次“濒死”体验。
图为死亡咖啡馆讨论话题
刚入职时,菲姐还只是一个20多岁的青春少女,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“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”。在这个人生阶段,人们都忙于追逐心中的“诗和远方”,死亡、病痛仿佛都还十分遥远。
正因如此,当菲姐连续一星期拉肚子时,她也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,直到有一次虚脱倒地,医院后,看着诊断书上的“急性胃肠炎”,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由于平时饮食作息的不规律和前期对病痛的不重视,菲姐的肠胃早已千疮百孔。腹泻、呕吐、肠胃痉挛等病痛常常轮番上阵,有时甚至一齐发力。在急性胃肠炎的折磨下,菲姐迅速地消瘦下去,往日的活力全无踪影。
日子一天天流逝,菲姐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。院方多次和菲姐的父母沟通,劝其转院,言下之意很明显:你们的女儿现在情况很危急,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,转院或许还会有一丝希望。
但菲姐父母坚持治疗的态度很坚决:“没关系,你们按照你们知道的继续治就行了。”
菲姐却没有父母那么坚持,到了后期,菲姐对于治愈已是几近绝望。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笼罩下,菲姐第一次体验到了“濒死”。用菲姐的话说:“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梦中,我好像飘起来了。我可以听见周围的声音,看见附近的人,但是我的意识并不清醒。”
事实上,医院刚下达病危通知书,菲姐正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,命悬一线。
不知过了多久,菲姐突然从梦中惊醒。床位已经从病房移至走廊,走廊里时不时有人走过。等意识完全清醒后,菲姐才意识到床边还坐着一个陌生的护工,护工怔怔地看着她,似乎很是惊讶于她的惊醒。
后来菲姐才知道,医院特意安排来观察她有无异常反应,以便及时告知院方。因为大家都以为她挺不过那一晚了。
“我想去上厕所。”
“我帮你拿个盆子吧。”
“不行,这里太多人了,我受不了。”
“你能走路吗?”
“我走不了,但是我可以扶着墙去。”
这是菲姐醒来后和外界的第一次交流。幽深的走廊里,菲姐一个人扶着墙,一步一步,踉踉跄跄地走到尽头的卫生间内。“上完厕所后,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”
经历了这一次的“濒死”后,在死神手里走过一遭的菲姐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,她开始接触各类与“死亡”有关的事情:辞去原来的工作,转而成为一名与死人打交道的殡葬师;进入广州十方缘,成为一名临终关怀义工……
和尸体对话,和临终患者对话。可以说,菲姐的每一天都在和“死亡”对话。在这种对话中,菲姐愈发认知到死亡的沉重。
图为活动现场
“我习惯和死去的人打交道,我看了太多不会说话的面孔,所以我想感受一下怎么和很会说话的人相处。在面对死人的时候,我有时会感觉到太沉重了,我想在死亡咖啡馆把这些东西消化掉。”
怀着对直面死亡的渴望,菲姐来到死亡咖啡馆,分享她的所见所闻,在不同生死观的碰撞中寻觅生命的真谛。
03于禁忌之外感悟生命在死亡咖啡馆内,不同年龄、地区、职业的人都可以找到。年,我在参加广州的另一家死亡咖啡馆开展的活动时,就遇见了一位来自成都的“死咖友”。暂且叫她Echo吧。和我之前遇到的很多“死咖友”一样,Echo也在进行着临终关怀的工作。
Echo曾在灾区和社区做志愿服务。不论是灾区的受害者,还是社区里饱受精神折磨的患者,都普遍面临着死亡的困扰,Echo的工作便是对其进行心理疏导。
而在做这些工作时,Echo其实也才拿到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不久。怀揣着救人的悲悯之心投身于心理咨询的事业,却在不久后便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。
“面对巨大的伤痛和死亡,我发现自己其实束手无策,毫无办法。我时常在想,如果自己是当事人,我可能还没有他们做得好。这样的我,拿什么去帮助他们呢?”Echo感觉自己仿佛遇到了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。
面对自己在残酷的现实和沉重的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无能,Echo决定做点什么。一次去上海的学习,让Echo接触到了死亡咖啡馆。“我想要做点和死亡相关的事情,什么都好。”这是当时Echo开办死亡咖啡馆的唯一想法。
有了想法之后,“行动派”Echo便立即着手相关工作:组织团队,选取店址,创立